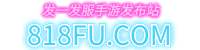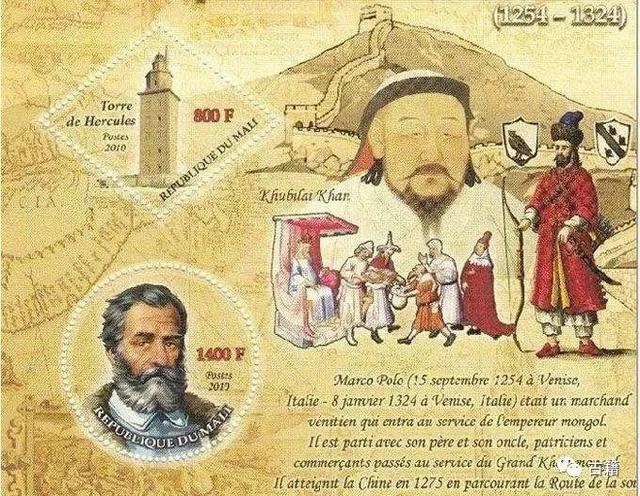
摘要:马可·波罗是出名的威尼斯游览家、商人赤金盛世传奇手游,因《马可·波罗游记》而享有盛名。然而赤金盛世传奇手游,后世关于他来华的实在性问题却不断争讼不竭。文章认为,他在游记中三次对中国麝与麝香做了较为精准的记述,不单纠正了此前西方人关于“麝香产自肚脐”的常识性错误,并且所记“麝无角”的特征也批改了伊斯兰文献中“麝有长角”的谬识。他对麝与麝香的存眷与记录,与其有关的档案中屡次关于麝香的信息存在着逻辑上的一致性。由此推知,马可·波罗极有可能来过中国,并为麝香常识的西传及工具文化交换做出了应有的奉献。
《马可·波罗游记》自问世起就备受存眷却也饱受争议,关于做者能否到过中国的争论更是不停于耳。中外学者操纵古今中外的材料,从多种角度研究,学术功效颇为丰盛。然而,上述问题似乎仍无定论。本文安身于《马可·波罗游记》中三次对中国的麝与麝香较为精准的记述,并连系与马可·波罗有关的档案中屡次呈现的关于麝香的信息,经研究认为他对麝与麝香比力熟悉且参与了麝香商业那种最能表现前现代期间全球化历程的经济活动。那也申明他极有可能来过中国,并为麝与麝香常识的西传及丝路交换做出了应有的奉献。
目前,国表里学术界尚无专文切磋马可·波罗与麝香的关系及其前现代的世界史意义。在3部马可·波罗学的权势巨子校本——C.穆勒和保罗·伯希和的校注本《寰宇记》、亨利·裕尔的《马可·波罗书》及其与考迪埃的《马可·波罗游记》合校本都有关于麝香问题的零散讨论,以及大卫·雅考比(David Jacoby)对马可·波罗返乡后的经商活动及其有关的档案研究,都为本文研究供给了有益的材料与启发。在那些研究的根底上,本文对马可·波罗与麝香的亲近关系停止了系统的研究,以期为马可·波罗来华寻找新的证据。
一、马可·波罗之前西方对麝香的认知与商业
在《马可·波罗游记》出书前,欧洲社会对麝和麝香的领会较少,根本上停留在丝绸之路传说风闻和宗教神话层面的认知上。据传,在亚历山大大帝迫使吐蕃臣服后,吐蕃赞普向其敬献4000维格尔的赤金及麝香。亚历山大拿出麝香的非常之一送给老婆罗克珊娜(Roxana),大部门麝香则分给他的伙伴。因为史籍中尚未发现此事确实切记载,且此为阿拉伯学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Ibn Khurradahbih,820一912)所记,因而我们只能暂且将之视为一则托伟人之名浪漫化麝香的传说。而早期基督教教父耶约姆(St.Jerome,347—420)将麝香上升到宗教层面加以神圣化,他说,麝香神圣而崇高,因为包罗麝香在内的香料是来自伊甸园的芳香。
据考证,生于埃及的希腊僧侣商人科斯马斯(Cosmas the Monk)是目前切当记载麝与麝香的西方第一人。他曾在印度洋地域游历与经商,到过印度与塔普罗巴乃岛(今斯里兰卡)。他在晚年所著《基督教世界风土志》(约公元545年)中提到麝是一种小动物,本地人称为喀斯杜里(Kasturi);猎人以箭射麝,待血集结在肚脐时将之割破。肚脐存储着称为麝香的香料。此处的“印度”应指喜马拉雅山,而非今斯里兰卡。大要因为缺乏深切的研究,故而他对麝香的产地做了模糊的处置。其次,他关于“麝香产自肚脐”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现实上,麝香是雄麝为吸引雌性而在其肚脐与生殖器之间的腺囊排泄物。不外,他的那些错误说法在西方社会传播甚广,曲至《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了“麝香产自麝囊”的准确记述。
虽然对麝和麝香的常识匮乏以至存在错误,但其实不影响古代欧洲人对麝香的神驰。因为他们认为麝香是来自伊甸园的芳香,有拯救、壮阳和催孕等奥秘成效,且利用麝香造做的高档香水是身份崇高的象征。因而,无论是希腊罗马期间的贵族仍是中世纪的教俗权贵,都巴望得到并利用麝香。在新航线开拓之前,麝香要颠末波斯、阿拉伯和埃及等中间商的屡次转运才气抵达欧洲,量少价高,且量量没有包管。虽然如斯,麝香商业在古代工具方的商业中仍连绵不停。
隋唐盛世期间,工具方商贸空前兴旺,操着阿拉伯语、波斯语、法兰克语和斯拉夫语等的商人携金带银经由陆路和海路来到中国,然后满载沉香、樟脑、肉桂及麝香等宝贵商货返回红海,运到埃及,再转销欧洲各地。在1187年前,从埃及进口的麝香次要在地中海东部的商贸中心阿卡(Arce)停止商业,曲至13世纪下半叶都是如斯。然后,商人又将之转运至君士坦丁堡,卖给罗马人或销售到法兰克王国。有记载说,1248年拆在长颈瓶中的36盎司麝香被从亚历山大里亚带到马赛交易。丰厚的利润招致造假活动流行,以致于市场上的麝香实假难辨。阿拉伯做家阿布尔一法德尔·贾法尔在《辨别好坏商品和伪造仿造商品须知书》(1175)中有专门章节介绍辨别实假麝香的办法。吉奥巴里的《关于泄露秘密的著做选》(1225年摆布出书)中称本身晓得造造假麝香的26种差别配方。
因为麝香量优量少而被付与了奇异的色彩,地中海列国之间经常将之做为外交与宗教的珍贵赠礼。据记载,埃及苏丹萨拉丁在1188年赠予拜占庭皇帝艾萨克二世(Isaac II Angelus,1185—1195年在位)100个麝香囊和一头雄性鹿。1262年,埃及苏丹扎希尔(al-Zahir,1260—1277)向君士坦丁堡的清实寺赠送麝香。那些交往集中在地中海东部地域,欧洲其他地域获得麝香的时机不是良多,尤其当穆斯林的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控造红海与地中海商业期间,欧洲人获得珍贵香料的难度更大。因而,麝香在15世纪之前的西方商品材料中少有呈现。略晚于马可·波罗的商人裴戈罗梯(Balducci Pegolotti,1290—1347)曾在《贸易指南》中提到麝香,却没有申明它在哪里停止交易。
二、《马可·波罗游记》关于麝与麝香的记载
13世纪,蒙古帝国在亚欧腹地敏捷兴起并四处攻城拔寨,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根本扫清了丝绸之路工具通顺的各类障碍(包罗穆斯林政权),实现了“人类之间最广阔而开放的一次握手”,引发了工具方空前的“全球信息交换”。1250—1350年也成为东方与西方互相“发现”的一个世纪。面临蒙前人强悍的侵袭,欧洲人在惊惧与猎奇中前去东方:布道士试图寻找打败穆斯林的盟友;商人则为商机纷至沓来。马可·波罗属于后者,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前去中国,并把沿途见闻记于游记中。做为商人,马可·波罗天然对易于运输且稀缺高贵的东方商品倍加留意,例如香料、宝石、珍珠、丝绸等。由此可知,他对优良麝香及其产地—吐蕃香带区的存眷天然也在情理之中。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三处关于麝与麝香的翔实记述:
第一处,第72章起首介绍了额里漱国(Ergiuul):该国“为大汗的属地,从属于唐古特省如此。然后谈及麝鹿以及麝香的取法:[FB\Z]此地有世界最良之麝香,请言其出产之法如下:此地有一种野兽,形如羚羊,蹄尾类羚羊,[L\V\TA\R]毛类鹿而较粗,头无角,[FB]口有四牙,上下各二,白如象牙,[VA\VB]长三指,薄而不厚,上牙下垂,下牙上峙。兽形身美。[V\Z\TL]鞑靼人云其名为古德里(Gudded)。[VB]马可旁边曾将此兽之头足带回威尼斯。[V]及盛于麝囊之中的麝香和一对牙齿。[VB]香气过浓,难以忍耐。[VB]猎人于新月升时往猎此兽,是亦其排泄麝香之时也。捕得此兽后,割其血袋。放到太阳下晒干。其浓郁香气即来自袋中之血。更优麝香来自于此。此肉可食,味甚佳。麝鹿大量被捕获。正如我告诉赤金盛世传奇手游你的,此地有量大且优良的麝香。”
第二处呈现在第115章吐蕃州,说“此大省为蒙前人所毁。[Z]此种产麝香之兽甚寡,其味漫衍全境,盖每月产麝一次。上次(七十一章)已曾言及此兽,脐旁有一胞,满盛血,每月胞满血出,是为麝香。此种地带有此类动物甚寡,麝味多处能够嗅觉。[VB\Z]他们用本身的语言称之为Gudderi,其肉味美。此种恶人畜犬(指藏獒—引者)甚多,犬大而丽,由是饶有麝香。”
第三处在第117章中的建德州(Caindu,裕尔认为它位于金沙江南端;德国粹者傅汉思认为它为四川西昌)中,“此地已臣属大汗……且有盐湖,以盐为币。[R]此地偏远,人很少有时机出卖诸如金、麝香以及其他工具,外商收买价极廉……[P]境内有产麝之兽古德里甚寡,[Z]所以出产麝香甚多。”
与当今关于麝与麝香的科学研究比力,上述三处记载的详细信息中仅两处不敷准确:一是“麝有四牙”与事实不符。麝鹿仅上颌有犬牙,薄而锐,即獠牙。而约公元851年按照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等人的见闻所汇编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别名《苏莱曼东游记》)则对麝的牙齿描写极为准确:“麝香鹿长着两个又细又白的犬齿,曲伸到脸部。一个犬齿的长度不到一个法特尔,形同象牙一般。”二是麝并不是每月而是每年排泄一次麝香。不外,那在波斯和阿拉伯的文献中也没有记录。
除此之外,《马可·波罗游记》与科斯马斯的《基督教世界风土志》《中国印度见闻录》及10世纪被誉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的马苏第(Masddi,896—956)的《黄金草原》相较,对中国包罗西藏麝与麝香的记述不单信息量大,且有严重打破。
起首,第72章中初次记录了麝“无角”的事实,推翻了阿拉伯世界“麝有长角”的错误。阿拉伯世界传播甚广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称,“麝香鹿跟我们阿拉伯的鹿非常类似,不单毛色、大小一样,并且双腿也是那样细长,蹄子也是分隔的,连头角的弯曲也都是一模一样”。因而,“麝有角”的说法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域持久传播,曲到20世纪末期伊朗修撰最权势巨子的《德胡达词典》仍在沿用“麝有长角”的错误说法。
其次,第115章中记录了“麝香在麝囊”而非肚脐的准确常识,突破了欧洲长达近8个世纪的错误说法。6世纪的科斯马斯犯了“麝香产自肚脐”的错误,次要是因为麝是一种胆怯、孤单而隐蔽的动物,人们少有时机察看其形体特征。麝香排泄过程更难亲目睹到。以致于宋代陆佃(1042—1102)所著《埤雅》卷3也认为“麝香来自肚脐”;清代杨春茂(1672—?)所著《重刊甘镇志》中也沿袭了那一说法。以至一些中国药师迄今还在传播“麝香是麝在张开香囊晒太阳时,引诱虫豸钻进囊内,突然封闭构成”的说法。而10世纪的马苏第已经晓得“优良的麝香乃在麝香囊里已经成熟,但尚未分开麝囊”。
以上关于马可·波罗记述的“麝无角”以及“麝香产自麝囊”两点准确常识,以至他犯的“麝有四牙”和“麝每月排泄一次麝香”的常识性错误都使得马可·波罗来华“否认论者”的概念不攻自破。若是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则无法晓得如斯详尽的麝鹿体貌特征及麝香产出部位;再则,若是他关于中国的常识都来自道听途说和某本波斯人的导游手册的话,那么他关于麝与麝香的信息很可能应照搬前人的说法,而不会犯上面提到的常识性错误。
第三,马可·波罗所记麝香产地及其品量也是准确的。他在第72章中认为额里漱国(即凉州府,裕尔认为它是阿拉善地域的一个古代城市;而伯希和认为它位于宁夏)“有世界最良之麝香”,第115章则记吐蕃“有此类动物甚寡,麝味多处能够嗅觉”。
马可·波罗所记中国西北地域出产更优量麝香可在古今中外许多文献中印证。例如,马苏第明白暗示吐蕃麝香比汉地的好,因为“吐蕃羊(即麝香羊)食芳香甘松茅和其他芳香动物,而汉地羊乃吃各类通俗草”,“吐蕃人把更好的麝香拆入从麝身上宰取来的皮郛里,做为礼品敬献给君主,供其利用”,且因为“商人很少能运走麝香”而愈加显得珍贵。布哈拉穆斯林游览家阿里·阿克巴尔(Seid Ali Akbar Khatai,1500—?)在《中国纪行》中提到此地麝香量优,“Kinjanfu(京兆府,今西安)、Kanju(甘州,今张掖)、Sekchou(肃州,今酒泉)和Dinkju(定州),在那几个城市盛产麝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列“麝脐香”一条,指出差别地域的麝香有好坏之分:“麝出西北者香结实;出东南者谓之土麝,亦可用,而力次之。南中灵猫囊,其气如麝,人以杂之。现代法国中亚史学者阿里·马扎海里(Aly Mazaheri,1914一1991)也说,吐蕃麝香因产量高、量量好而为世人所知。据现代学者考证,麝次要散布在喜马拉雅山到阿尔泰山,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地域。此中,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域的麝喜吃冷杉、雪松、柏树等带有香味的植被,故麝香品量更佳。
第四,第115章中提到吐蕃麝香味道浓郁(“麝味多处能够嗅觉”),那在中外文献中也得到了佐证。萨珊王朝6世纪的文献《科斯洛埃斯二世及其随从官》提到,吐蕃麝香与印度的“龙涎香”“波斯的玫瑰齐名,是“最香的香精”。宋代的《图经本草》也说:“香有三等,第一生香,名遗香,乃麝自剔出者,然极罕见,价同明珠。其香聚处,远近牛山濯濯或焦黄也。今人带香过园林瓜果皆不实,是其验也。其次是脐香,乃捕得杀取之。其三心结香,乃麝见大兽捕遂惊畏失心,狂走坠死。”关于那个问题,李时珍也解释说,因为“麝之香气远射,故谓之麝。或云麝父之香来射,故名,亦通”。
第五,第115章吐蕃州中记述了藏獒猎麝之事。迄今所见,马可·波罗也是第一位记载藏獒猎麝的欧洲人。那一记载在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中得到佐证:“在西藏山区有一种良狗,西藏人用它向皇帝进贡。在土耳其,苏丹也有那种狗,被称为萨珊尼,据说是西藏种。麝就是用那种狗去猎取的。”用藏獒获取麝鹿的办法曲到16世纪还在利用,为路过此地的列国商贾所知。
《马可·波罗游记》还记载了长江上游一带盛产麝香,出格是以盐为币买卖麝香的风俗。第117章中提到今四川西昌建德州也盛产麝香,因而地偏远,外商以盐为币购置廉价麝香的事实。那也是西方人对该地那种特殊商贸活动的最早记载。5个世纪后,近代西方探险家、法国神父古伯察(Évariste Régis Uuc,1813—1860)曾在藏东察雅的石板沟目击了麝香的产量及交易的情况:“石板沟中盛产麝香……,谁在其他处所都没见过那么多。……那里的居民把麝香做为一种与中原人处置十分有利可图的商业商品。”他并未提及以盐代币的商业行为,或许此时那种做法已经消匿。
由上推知,马可·波罗若没有到过中国,很难将麝鹿的体貌特征、活动区域、生活习性,麝香的产出部位、获取办法及好坏,以至建德州以盐代币的商业体例等信息描写得如斯准确。能够说,那是西方人初次将麝鹿的生活习性与麝香的消费如斯完好详尽地介绍到欧洲,批改了许多商旅及医学界的“常识性”错误。在那种意义上说,马可·波罗对丝绸之路的工具文化交换做出了奇特奉献。
三、返乡后的马可·波罗与麝香
麝香做为笨重易带且价值高、利润丰厚的珍贵商品,不断遭到亚洲、非洲和欧洲商人的喜爱。然而,即使在欧亚交通网极兴旺的蒙元时代,亚洲的麝香运抵欧洲也必需颠末中亚的波斯、阿拉伯或埃及中间商之手。因而,欧洲商人巴望能间接从中国获取麝香等宝贵香料。做为商人的马可·波罗肯定深知那种豪侈品商业背后的可不雅利润。因而,他在返乡后对麝香商业表示出了浓重的兴趣。
以至有学者认为,马可·波罗早在中国甘州(今张掖)时就应该做过包罗麝香在内等香料的生意。因为他在游记中的“甘州”(今张掖)一节中说,为了做生意,他与父亲、叔叔在甘州待了一年。那种揣测不无事理。甘州一带也盛产优良麝香,由此转运和田,再输往波斯。清代的钟赓起编撰的《甘州府志》和杨春茂编著的《重刊甘镇志》中都在“物产”中记载了此地消费麝和麝香。也许恰是在此经商一年,马可·波罗才有时机近间隔接触到麝与麝香,并把察看到的和本地听闻记录下来。
若是马可·波罗在甘州就处置过麝香买卖属于合理性揣测的话,那么他在返回威尼斯后停止过麝香商业则是有据可循。现保留于威尼斯国立圣马可藏书楼( Venice National Marciana Library )关于马可·波罗的诉讼案、他本人及其家族成员的遗嘱,以及遗产清单等5份贵重的档案文献,都有关于麝香的信息,有力地申明以他为首的波罗家族停止过包罗麝香在内的东方贵重商品的商业活动
起首,马可·波罗的叔叔马菲奥(Maffeo Polo)在1310年2月6日起草的遗嘱中提到两人配合销售麝香之事,曾把一笔钱委托给3个贩运商代购麝香。然而,那些贩运商似乎并没有信守许诺。一个名叫马凯斯诺(Marchesino Berengo)的贩运商的儿子保罗·贝伦戈(Paolo Berengo)替他父亲赔付了马可·波罗及其叔父一笔相当于400镑的威尼斯金币(piccoli),此中马可·波罗占2/3的份额。此外,贩运商还需补偿他们86萨觉(saggi)的麝香。马菲奥还把其他两位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债务人名字也写在了那份遗嘱之中。至于后面他们能否偿金或麝香,并没有发现相关记录。
其次,马可·波罗本人也有一桩关于麝香的诉讼案件。1310年4月,他把属于本身及同父异母兄弟乔瓦尼(Giovannino)的1.5磅(相当于451.84格罗西[grosso])的麝香,委托给一名叫保罗·吉拉尔多(Paolo Girardo)的商人销售,契约中声明的价格是每磅2.61杜卡特(ducats)金币,受托人将获取那笔交易利润的一半。然而,保罗在次年3月返回威尼斯后,不单没有把卖掉的半磅麝香的收益交给马可·波罗,并且其余1磅麝香也不翼而飞。于是,马可·波罗把保罗告上了法庭。1311年3月,法官判决马可·波罗胜诉,要求保罗补偿胜诉方应得的利润和丧失的麝香;若是败诉方不克不及及时补偿胜诉方,将根据威尼斯的法令判处监禁之刑,且服刑期间费用自理。
再次,马可·波罗还曾把麝香做为贷款的重要抵押品。在上述麝香案判决的统一年,香料经销商瓦勒(Valor)的老婆尼科莱塔(Nicoletta)声明,本身偿还了为马可·波罗暂时保管的各类珍贵商品,包罗1萨觉和7.49格罗西的麝香。两家很可能有生意往来,而那些商品可能是马可·波罗给经销商及老婆贷款的抵押品。除了生意上的伙伴关系外,他们还应该有十分亲密的私家关系。因为尼科莱塔在1314年指定马可·波罗及其同父异母兄弟斯蒂芬(Stefanno)做为她遗嘱的施行人。由此能够大概推知,马可·波罗可能在威尼斯商人圈子中建起了一个寒暄收集,并在此中颇有声望。
第四,马可·波罗在1324年逝世时,遗产中有三箱已从麝囊中取出的麝香,此中两箱被列入了他的财政清单。一箱估价5.5镑或55杜卡特金币,另一箱估价10镑或100杜卡特金币,第三箱麝香估价6.2英镑或62杜卡特金币。按照马可·波罗声明的价格(每榜2.61杜卡特金币)计算,那三箱麝香总量超越83磅,价值约为217杜卡特金币(约相当于705克黄金)。那些数量大、价值高的麝香显然不是留给本身或家人利用的,那申明麝香在其大规模的经商活动中应占有不小的比重。与此同时,在此中一个贮藏麝香的箱子中还发现了一个拆麝鹿皮的袋子,申明他喜好保藏与麝有关的一些工具。正如《马可·波罗游记》(VB)所记,“马可·波罗旁边曾将风干的麝的头骨和脚骨带回威尼斯,还有拆在麝囊中的麝香”。
第5份与麝香有关的档案是马可·波罗女儿的遗产告状书。按照马可·波罗的遗嘱,除了捐赠给教会的部门财产外,没有儿子的他并没有根据习惯性做法将遗产分给其家族的其他男性后嗣,而是分给了老婆及3个女儿。此中,大女儿芳提娜(Fantina)没有子女,在丈夫身后向丈夫家索要父亲留给本身的遗产,在1354年向威尼斯法庭提交的诉讼中提到了父亲的麝香。由此能够推知,芳提娜所拥有的麝香应该就是上文中提到的三箱麝香中的一部门。
以上5份关于马可·波罗与麝香有关的珍贵档案能够做为他游记之外证明其来华可能性的极好证据。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还发现,马可·波罗财富清单的档案中还有他极有可能到过中国的其他证据,好比7.229公斤白色蚕茧、12.049公斤丝绸、4块鞑靼可汗颁布的蒙古“金牌”(Paiza)通行证、金线织锦并饰有羽毛和珍珠的蒙古头饰,以及“鞑靼式样”的白色袍子等。
四、余论
马可·波罗在蒙前人创始的全球化时代,怀着猎奇求知的心态来到东方,并“照实”记录了本身的见闻。然而,他的见闻其实不为他的基督教教友们所承受和承认,故被谑称为“说谎大王”,以至在临末病榻上还被要求为本身的“谎话”忏悔!虽然他在书中那么切确地记载了麝以及麝香的丰硕常识,但曲到18世纪早期,关于麝香的产地及其香味的原理对其时的欧洲人来说,仍是一个谜。那也申明《马可·波罗游记》并没有被同时代及以后4个多世纪里的欧洲人所遍及承受。
事实上,马可·波罗所记物种、货源、运营商品及档案文献为其来华实在性供给了较为可信的证据。做为精明的商人,他对中国西部地域(包罗吐蕃)的麝及麝香有着强烈的猎奇心,很可能对麝香商业停止过较为深切的查询拜访,才可能有较为切确的记述。他不单纠正了此前西方人关于“麝香产自肚脐”的错误,并且所记“麝无角”的特征也突破了伊斯兰文献中“麝有长角”的谬识。在返回故土后,他本人及其家族持久处置麝香商业,并在诉讼案宗、合做伙伴记录、遗产清单以及其留给女儿的遗产等档案中都提到了麝香。那些记述与其活动之间在逻辑上存在着合理性,也能够做为他极有可能到过中国的佐证。简言之,马可·波罗及其游记不只对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关于麝与麝香的错误认识停止了批改,也为之西传做出了重要奉献,更为重要的是,为近代以前的欧洲人认识和领会东方开启了一扇窗。
姬庆红,兰州大学汗青文化学院传授,剑桥大学拜候学者,主攻古罗马史、中外交换史。著\译马可·波罗册本两部。在《光亮日报》《古代文明》等刊物颁发论文多篇,主持及参与国度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文章原载于《中国藏学》2020年第1期。
- 上一篇: 原始1.76传奇手游原始复古传奇176手游
- 下一篇: 关于传奇手游单机版破解版的信息
猜你喜欢
- 2024-09-07老款传奇手游传奇永恒同款手游
- 2024-09-07(烈焰传奇手游下载)烈焰传奇手机游戏
- 2024-09-07传奇类型的手机游戏传奇类手游
- 2024-09-07新传奇手游:2023最新的传奇手游推荐 2023有哪些新传奇手游
- 2024-09-072合1合成版传奇手游二合一传奇手游
- 2024-09-07传奇手游新区:传奇风云龙城决神威秘境攻略!虎符传奇手游神威突破攻略!